6月17日上午,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功举办“财政行为与博弈论应用研讨会”。研讨会采用“主旨演讲+问答交流”的方式开展。研讨会特邀我校学术委员会主席李俊生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希伯来大学理性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顶级博弈论学者Shmuel Zamir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曹志刚教授和北京大学颜建晔副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明星主持研讨会。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全体师生及校内外师生参加研讨会。

李俊生教授首先致开幕词。李俊生教授指出,互动是财政行为研究的核心。所以,对财政行为的研究不能仅从政府这一方面展开,而要考虑多方互动的行为结果。博弈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常被用于交互式的决策研究,因而可以为探索财政行为的互动性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框架。李俊生教授希望本次研讨会能成为一个交流观点和激发新想法的平台。

李俊生教授发表题为“中国财政行为者的市场特征”的主旨演讲。李俊生教授指出,我国当代主流财政理论基本上就是英美财政理论的翻版,当下,该理论存在与实践严重脱节、解释力和预测力严重弱化等问题。更严重的是,我国主流财政理论对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基本理论问题解释无力,并且对于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等重大体制与政策决策问题,拿不出有学理支撑建议。李俊生教授认为,鉴于主流财政理论存在种种缺陷,财政科学发展的出路在于摆脱主流财政理论个人主义分析范式、经济学化的理论体系与核心概念体系等经济学属性。据此李俊生教授在演讲中介绍了“新市场财政学”,以此重构科学的财政理论体系。李俊生教授指出,新市场财政学理论体系下,财政科学属于复合型、跨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而非单纯的经济学问题。因此,财政科学应当是研究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为主要目的的财政行为及财政关系。
基于对财政科学目标的判断,李俊生教授对财政科学进行了重新定义。李俊生教授指出,财政学是研究政府如何在市场平台上与社会组织、企业和家庭互动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复合型社会科学。一言以蔽之,重新定义的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应当是“社会共同需要理论”,而不能是市场失灵理论。基于社会共同需要理论基础,李俊生教授提出了经重构的财政科学—即新市场财政学—的理论框架:市场平台观。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家庭在市场平台上遵守一套相同的市场规则,按照市场的通行方式来实现各自的目标。政府在市场平台中是以一个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于其他市场主体的互动。李俊生教授最后指出,希望新市场财政学的理论范式能与博弈论的研究相互融合,相互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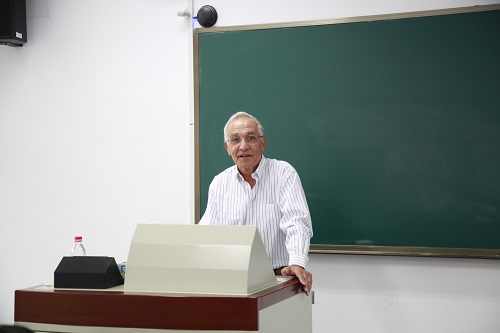
Shmuel Zamir教授发表题为“机制设计与财政政策”的主旨演讲。Zamir教授指出,博弈论是一个用来研究分析涉及多主体的互动性决策的数学工具。显然,财政问题是博弈问题,涉及的多主体至少包括政府、经济单位、个人等;后两者要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做出反应,政府又根据反馈做出新决策。财政政策出台的目的在于实现特定目标,并假定“财政政策面向的其他对象要按照特定的方式行动”。然而,其他对象作为独立的决策者,有各自的偏好,且不能完全被政府所知晓。因此,政府假定的其他对象行动方式与实际情况必然存在偏离,政府若想强制将其他对象的行动方式规范到政府期待的模式上,则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Zamir教授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需要通过博弈论来进行机制设计来解决问题。机制设计的基本概念是“找寻一系列的规则构造一个博弈,使得在这一博弈下参与者有动机按照能达成期待结果的方式行动”,即“找到一种博弈,其均衡状态(最好是占优策略)为目标结果”。此时,达成目标结果的方式行动将构成纳什均衡,任何参与人都不会有动机偏离这些行动。Zamir教授以例证的方式讲解如何用博弈论的观点设计机制。他指出,二级价格拍卖(Second-Price Auction)就是一个很好的机制,能够直接显示出价人的真实偏好。在这一机制下对于任何一种销售机制和该机制的均衡,都存在一种与激励相容的、具有相同均衡的直接销售机制。换言之,二级价格拍卖这种机制能够使得竞标者以真实意愿报价成为均衡。

曹志刚教授发表题为“合作函数”的主旨演讲。曹志刚教授指出,合作博弈论相对于非合作博弈论属于抽象程度更高的模型,建模时不需要太多博弈过程信息。但合作博弈论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当核不空的时候通常比较大,以及作为集合函数的合作博弈高度组合,对于多数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技术障碍。曹志刚教授提出的研究方法为直接研究相应问题背后的称之为“合作函数”的普通函数。曹志刚教授认为,合作函数方法的优势在于表示起来更加简便,处理起来更加简洁,并且可以包含更多信息。通过直接分析被称为合作函数的底层函数,而不是通过分析诱导的合作博弈,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合作博弈。

颜建晔副教授发表题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机和‘政策负担’”的主旨演讲。颜建晔副教授提到,学界普遍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归因于缺乏自主权、产权界定不清、激励机制不佳。但改革30多年后,低效的情况依然存续。颜建晔副教授提出问题:“为什么经典的激励理论在中国国企改革中不适用?”颜建晔副教授认为,所有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不能避免委托代理问题以及道德风险。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三个条件:(1)企业处于竞争性行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和市场中,平均盈利能力是公共知识;(2)专业经理人市场是成熟和竞争性的;(3)审计机关的市场竞争保障其公正性。颜建晔副教授指出,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实施时缺乏三个条件,所以“所有制”改革不够成功。颜建晔副教授认为,缺少这三个条件的内在约束是: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主导份额来自计划经济中的对比较优势否认的发展战略,所以在资本稀缺时,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了资源扭曲与错位。“国家所有制”使资源的集中朝着与市场相反的方向进行。因此,国有企业只得容纳更多工人,并承担“政策性负担”。颜建晔副教授用一个初步的数理经济模型展示将“政策性负担”引入经典的激励理论模型就得不到教科书和文献中的传统激励结果。